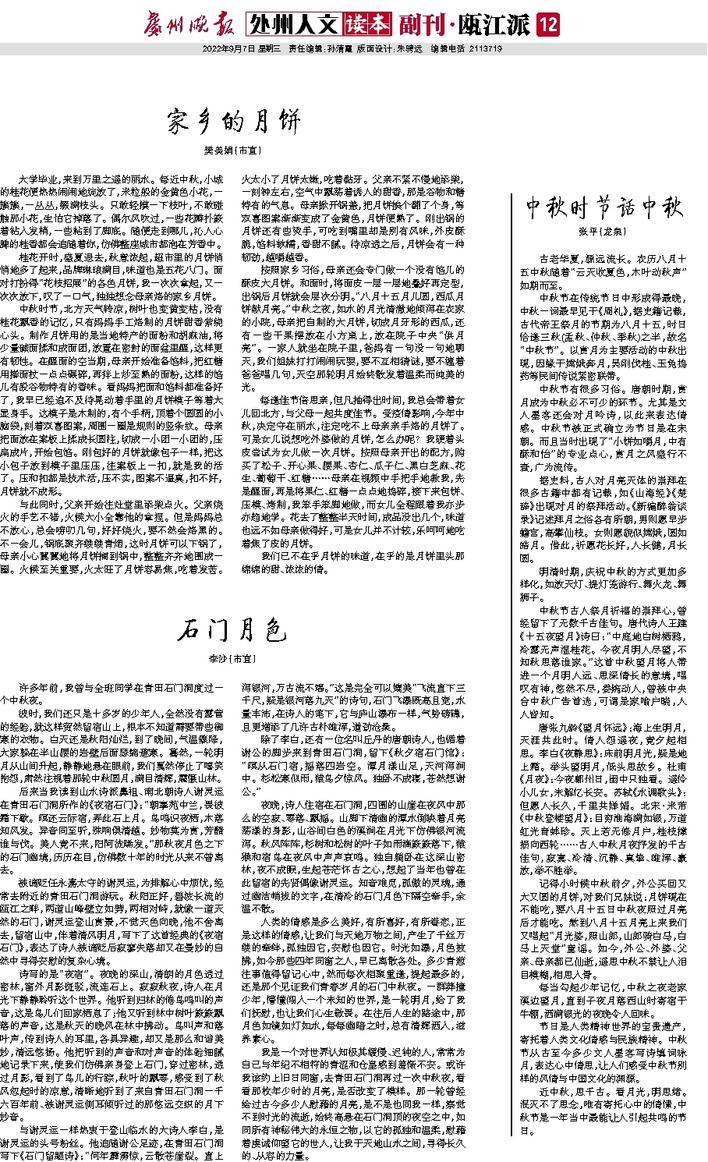李沙(市直)
许多年前,我曾与全班同学在青田石门洞度过一个中秋夜。
彼时,我们还只是十多岁的少年人,全然没有露营的经验,就这样贸然留宿山上,根本不知道需要带些御寒的衣物。白天还是秋阳灿烂,到了晚间,气温骤降,大家躲在半山腰的岩壁后面瑟缩避寒。蓦然,一轮明月从山间升起,静静地悬在眼前,我们戛然停止了嘻笑抱怨,肃然注视着那轮中秋圆月,满目清辉,震慑山林。
后来当我读到山水诗派鼻祖、南北朝诗人谢灵运在青田石门洞所作的《夜宿石门》:“朝搴苑中兰,畏彼霜下歇。暝还云际宿,弄此石上月。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异音同至听,殊响俱清越。妙物莫为赏,芳醑谁与伐。美人竟不来,阳阿徒晞发。”那秋夜月色之下的石门幽境,历历在目,仿佛数十年的时光从来不曾离去。
被谪贬任永嘉太守的谢灵运,为排解心中烦忧,经常去附近的青田石门洞游玩。秋阳正好,碧波长流的瓯江之畔,两道山峰壁立如劈,两相对峙,就像一道天然的石门,谢灵运登山赏景,不觉天色向晚,他不舍离去,留宿山中,伴着清风明月,写下了这首经典的《夜宿石门》,表达了诗人被谪贬后寂寥失落却又在曼妙的自然中寻得安慰的复杂心境。
诗写的是“夜宿”。夜晚的深山,清朗的月色透过密林,窗外月影斑驳,流连石上。寂寂秋夜,诗人在月光下静静聆听这个世界。他听到归林的倦鸟鸣叫的声音,这是鸟儿们回家栖息了;他又听到林中树叶簌簌飘落的声音,这是秋天的晚风在林中拂动。鸟叫声和落叶声,传到诗人的耳里,各具异趣,却又是那么和谐美妙,清远悠扬。他把听到的声音和对声音的体验细腻地记录下来,使我们仿佛亲身登上石门,穿过密林,透过月影,看到了鸟儿的行踪,秋叶的飘零,感受到了秋风忽起时的凉意,清晰地听到了来自青田石门洞一千六百年前、被谢灵运侧耳倾听过的那悠远交织的月下妙音。
与谢灵运一样热衷于登山临水的大诗人李白,是谢灵运的头号粉丝。他追随谢公足迹,在青田石门洞写下《石门留题诗》:“何年霹雳惊,云散苍崖裂。直上泻银河,万古流不竭。”这是完全可以媲美“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诗句,石门飞瀑既高且宽,水量丰沛,在诗人的笔下,它与庐山瀑布一样,气势磅礴,且更增添了几许古朴雄浑,遒劲沧桑。
除了李白,还有一位名叫丘丹的唐朝诗人,也循着谢公的脚步来到青田石门洞,留下《秋夕宿石门馆》:“暝从石门宿,摇落四岩空。潭月漾山足,天河泻涧中。杉松寒似雨,猿鸟夕惊风。独卧不成寝,苍然想谢公。”
夜晚,诗人住宿在石门洞,四围的山崖在夜风中那么的空寂、零落、飘摇。山脚下清幽的潭水倒映着月亮荡漾的身影,山谷间白色的溪涧在月光下仿佛银河流泻。秋风阵阵,杉树和松树的叶子如雨滴簌簌落下,猿猴和宿鸟在夜风中声声哀鸣。独自躺卧在这深山密林,夜不成眠,生起苍茫怀古之心,想起了当年也曾在此留宿的先贤偶像谢灵运。知音难觅,孤傲的灵魂,通过幽洁峭拔的文字,在清冷的石门月色下隔空牵手,余温不散。
人类的情感是多么美好,有所喜好,有所眷恋,正是这样的情感,让我们与天地万物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牵绊,孤独因它,安慰也因它。时光如瀑,月色披拂,如今那些四年同窗之人,早已离散各处。多少青葱往事值得留记心中,然而每次相聚重逢,提起最多的,还是那个见证我们青春岁月的石门中秋夜。一群莽撞少年,懵懂闯入一个未知的世界,是一轮明月,给了我们抚慰,也让我们心生敬畏。在往后人生的路途中,那月色如镜如灯如水,每每幽暗之时,总有清辉洒入,滋养素心。
我是一个对世界认知极其缓慢、迟钝的人,常常为自己与年纪不相符的青涩和仓皇感到羞惭不安。或许我该约上旧日同窗,去青田石门洞再过一次中秋夜,看看那枚年少时的月亮,是否改变了模样。那一轮曾经给过古今多少人慰藉的月亮,是不是也同我一样,察觉不到时光的流逝,始终高悬在石门洞顶的夜空之中,如同所有神秘伟大的永恒之物,以它的孤独和温柔,慰藉着虔诚仰望它的世人,让我于天地山水之间,寻得长久的、从容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