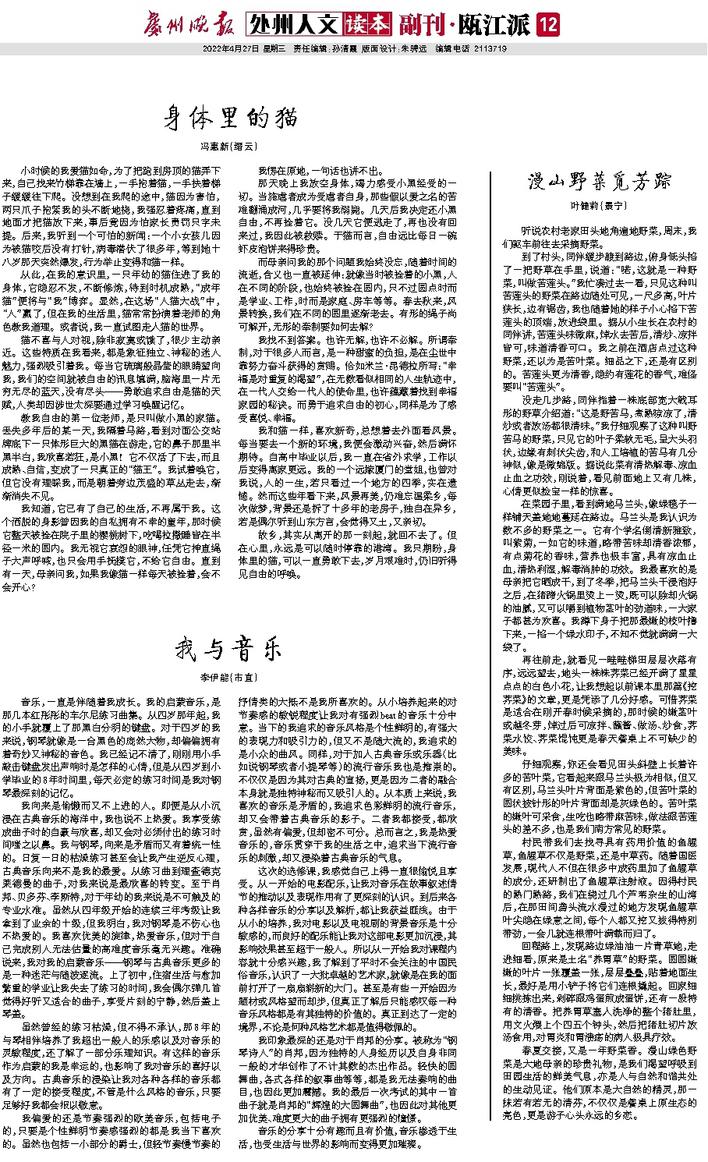冯惠新(缙云)
小时候的我爱猫如命,为了把跑到房顶的猫弄下来,自己找来竹梯靠在墙上,一手抱着猫,一手扶着梯子缓缓往下爬。没想到在我爬的途中,猫因为害怕,两只爪子抱紧我的头不断地挠,我强忍着疼痛,直到地面才把猫放下来,事后竟因为怕家长责罚只字未提。后来,我听到一个可怕的新闻:一个小女孩儿因为被猫咬后没有打针,病毒潜伏了很多年,等到她十八岁那天突然爆发,行为举止变得和猫一样。
从此,在我的意识里,一只年幼的猫住进了我的身体,它隐忍不发,不断修炼,待到时机成熟,“成年猫”便将与“我”博弈。显然,在这场“人猫大战”中,“人”赢了,但在我的生活里,猫常常扮演着老师的角色教我道理。或者说,我一直试图走入猫的世界。
猫不喜与人对视,除非寂寞或饿了,很少主动亲近。这些特质在我看来,都是象征独立、神秘的迷人魅力,强烈吸引着我。每当它琉璃般晶莹的眼睛望向我,我们的空间就被自由的讯息填满,脑海里一片无穷无尽的蓝天,没有尽头——勇敢追求自由是猫的天赋,人类却因涉世太深要通过学习唤醒记忆。
教我自由的第一位老师,是只叫做小黑的家猫。丢失多年后的某一天,我隔着马路,看到对面公交站牌底下一只体形巨大的黑猫在游走,它的鼻子那里半黑半白,我欣喜若狂,是小黑!它不仅活了下去,而且成熟、自信,变成了一只真正的“猫王”。我试着唤它,但它没有理睬我,而是朝着旁边茂盛的草丛走去,渐渐消失不见。
我知道,它已有了自己的生活,不再属于我。这个洒脱的身影曾因我的自私拥有不幸的童年,那时候它整天被拴在院子里的樱桃树下,吃喝拉撒睡皆在半径一米的圆内。我无视它哀怨的眼神,任凭它抻直绳子大声呼喊,也只会用手抚摸它,不给它自由。直到有一天,母亲问我,如果我像猫一样每天被拴着,会不会开心?
我愣在原地,一句话也讲不出。
那天晚上我放空身体,竭力感受小黑经受的一切。当施虐者成为受虐者自身,那些假以爱之名的苦难翻涌成河,几乎要将我溺毙。几天后我决定还小黑自由,不再拴着它。没几天它便逃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过,我因此被救赎。于猫而言,自由远比每日一碗虾皮泡饼来得珍贵。
而母亲问我的那个问题我始终没忘,随着时间的流逝,含义也一直被延伸:就像当时被拴着的小黑,人在不同的阶段,也始终被拴在圆内,只不过圆点时而是学业、工作,时而是家庭、房车等等。春去秋来,风景转换,我们在不同的圆里逐渐老去。有形的绳子尚可解开,无形的牵制要如何去解?
我找不到答案。也许无解,也许不必解。所谓牵制,对于很多人而言,是一种甜蜜的负担,是在尘世中靠努力奋斗获得的赏赐。恰如米兰·昆德拉所写:“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望”,在无数看似相同的人生轨迹中,在一代人交给一代人的使命里,也许蕴藏着找到幸福家园的秘诀。而勇于追求自由的初心,同样是为了感受喜悦、幸福。
我和猫一样,喜欢新奇,总想着去外面看风景。每当要去一个新的环境,我便会激动兴奋,然后满怀期待。自高中毕业以后,我一直在省外求学,工作以后变得离家更远。我的一个远嫁厦门的堂姐,也曾对我说,人的一生,若只看过一个地方的四季,实在遗憾。然而这些年看下来,风景再美,仍难忘温柔乡,每次做梦,背景还是拆了十多年的老房子,独自在异乡,若是偶尔听到山东方言,会觉得又土,又亲切。
故乡,其实从离开的那一刻起,就回不去了。但在心里,永远是可以随时停靠的港湾。我只期盼,身体里的猫,可以一直勇敢下去,岁月艰难时,仍旧听得见自由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