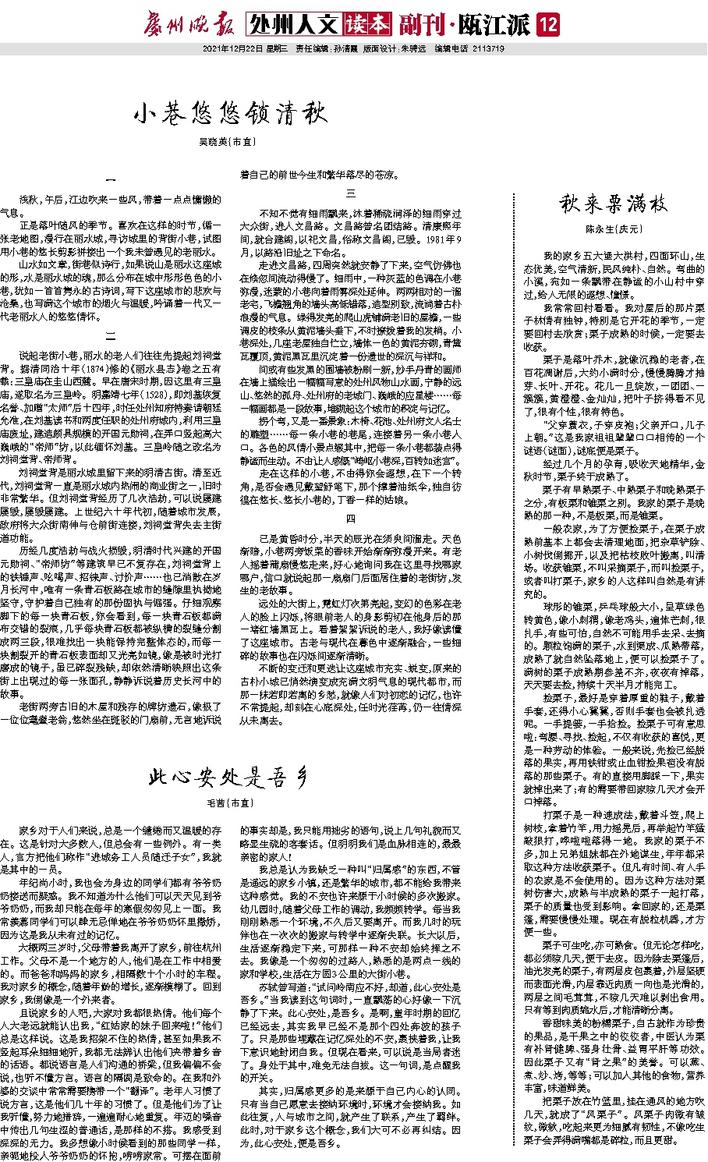毛茜(市直)
家乡对于人们来说,总是一个缱绻而又温暖的存在。这是针对大多数人,但总会有一些例外。有一类人,官方把他们称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年纪尚小时,我也会为身边的同学们都有爷爷奶奶接送而疑惑。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可以天天见到爷爷奶奶,而我却只能在每年的寒假匆匆见上一面。我常羡慕同学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在爷爷奶奶怀里撒娇,因为这是我从未有过的记忆。
大概两三岁时,父母带着我离开了家乡,前往杭州工作。父母不是一个地方的人,他们是在工作中相爱的。而爸爸和妈妈的家乡,相隔数十个小时的车程。我对家乡的概念,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模糊了。回到家乡,我倒像是一个外来者。
且说家乡的人吧,大家对我都很热情。他们每个人大老远就能认出我,“红姑家的妹子回来啦!”他们总是这样说。这是我招架不住的热情,甚至如果我不竖起耳朵细细地听,我都无法辨认出他们夹带着乡音的话语。都说语言是人们沟通的桥梁,但我偏偏不会说,也听不懂方言。语言的隔阂是致命的。在我和外婆的交谈中常常需要携带一个“翻译”。老年人习惯了说方言,这是他们几十年的习惯了。但是他们为了让我听懂,努力地措辞,一遍遍耐心地重复。年迈的嗓音中传出几句生涩的普通话,是那样的不搭。我感受到深深的无力。我多想像小时候看到的那些同学一样,亲昵地投入爷爷奶奶的怀抱,唠唠家常。可摆在面前的事实却是,我只能用拙劣的语句,说上几句礼貌而又略显生疏的客套话。但明明我们是血脉相连的,最最亲密的家人!
我总是认为我缺乏一种叫“归属感”的东西,不管是遥远的家乡小镇,还是繁华的城市,都不能给我带来这种感觉。我的不安也许来源于小时候的多次搬家。幼儿园时,随着父母工作的调动,我频频转学。每当我刚刚熟悉一个环境,不久后又要离开。而我儿时的玩伴也在一次次的搬家与转学中逐渐失联。长大以后,生活逐渐稳定下来,可那样一种不安却始终挥之不去。我像是一个匆匆的过路人,熟悉的是两点一线的家和学校,生活在方圆3公里的大街小巷。
苏轼曾写道:“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当我读到这句词时,一直飘荡的心好像一下沉静了下来。此心安处,是吾乡。是啊,童年时期的回忆已经远去,其实我早已经不是那个四处奔波的孩子了。只是那些埋藏在记忆深处的不安,裹挟着我,让我下意识地封闭自我。但现在看来,可以说是当局者迷了。身处于其中,难免无法自拔。这一句词,是点醒我的开关。
其实,归属感更多的是来源于自己内心的认同。只有当自己愿意去接纳环境时,环境才会接纳我。如此往复,人与城市之间,就产生了联系,产生了羁绊。此时,对于家乡这个概念,我们大可不必再纠结。因为,此心安处,便是吾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