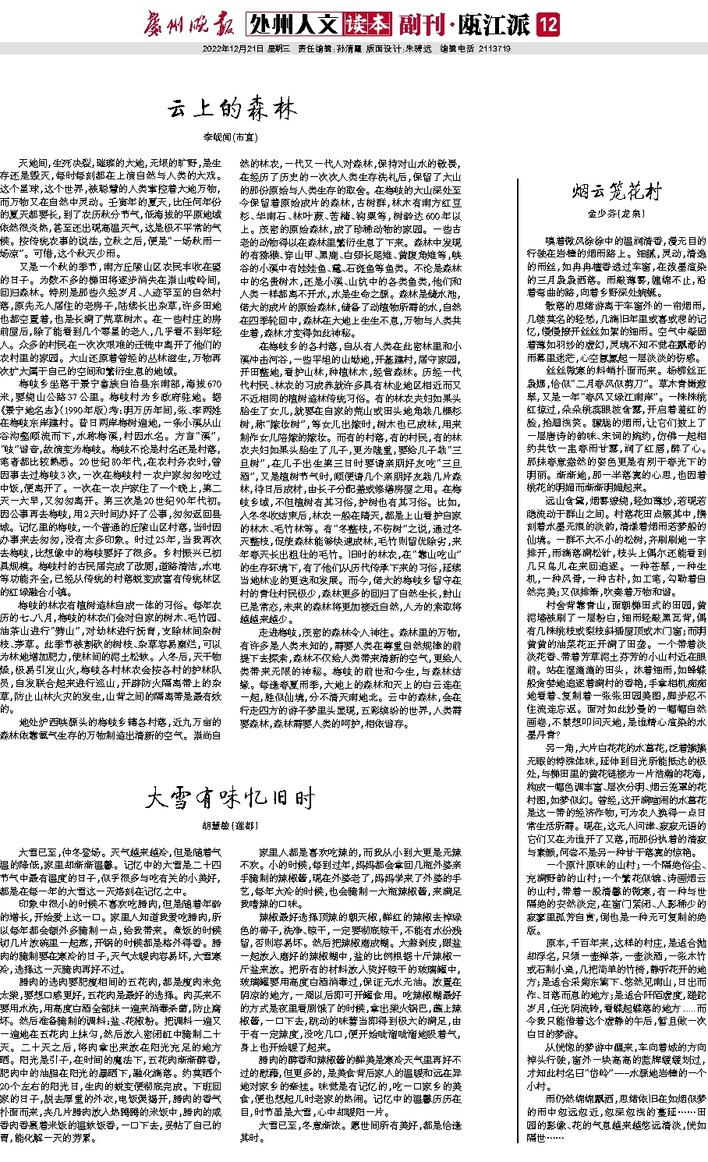李岘闻(市直)
天地间,生死决裂,璀璨的大地,无垠的旷野,是生存还是毁灭,每时每刻都在上演自然与人类的大戏。这个星球,这个世界,被聪慧的人类掌控着大地万物,而万物又在自然中灵动。壬寅年的夏天,比任何年份的夏天都要长,到了农历秋分节气,低海拔的平原地域依然很炎热,甚至还出现高温天气,这是极不平常的气候。按传统农事的说法,立秋之后,便是“一场秋雨一场凉”。可惜,这个秋天少雨。
又是一个秋的季节,南方丘陵山区农民丰收在望的日子。为数不多的梯田将逐步消失在崇山峻岭间,回归森林。特别是那些久经岁月、人迹罕至的自然村落,原先无人居住的老房子,陆续长出杂草,许多田地也都空置着,也是长满了荒草树木。在一些村庄的房前屋后,除了能看到几个零星的老人,几乎看不到年轻人。众多的村民在一次次艰难的迁徙中离开了他们的农村里的家园。大山还原着曾经的丛林滋生,万物再次扩大属于自己的空间和繁衍生息的地域。
梅岐乡坐落于景宁畲族自治县东南部,海拔670米,要绕山公路37公里。梅岐村为乡政府驻地。据《景宁地名志》(1990年版)考:明万历年间,张、李两姓在梅岐东岸建村。昔日两岸梅树遍地,一条小溪从山谷沟壑顺流而下,水称梅溪,村因水名。方言“溪”,“岐”谐音,故演变为梅岐。梅岐不论是村名还是村落,笔者都比较熟悉。20世纪80年代,在农村务农时,曾因事去过梅岐3次,一次在梅岐村一农户家匆匆吃过中饭,便离开了。一次在一农户家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大早,又匆匆离开。第三次是20世纪90年代初。因公事再去梅岐,用2天时间办好了公事,匆匆返回县城。记忆里的梅岐,一个普通的丘陵山区村落,当时因办事来去匆匆,没有太多印象。时过25年,当我再次去梅岐,比想像中的梅岐要好了很多。乡村振兴已初具规模。梅岐村的古民居完成了改厕,道路清洁,水电等功能齐全,已经从传统的村落蜕变成富有传统林区的红绿融合小镇。
梅岐的林农有植树造林自成一体的习俗。每年农历的七、八月,梅岐的林农们会对自家的树木、毛竹园、油茶山进行“劈山”,对幼林进行抚育,支除林间杂树枝、茅草。此季节被割砍的树枝、杂草容易糜烂,可以为林地增加肥力,使林间的泥土松软。入冬后,天干物燥,极易引发山火,梅岐各村林农会按各村的护林队员,自发联合起来进行巡山,开辟防火隔离带上的杂草,防止山林火灾的发生,山背之间的隔离带是最有效的。
地处炉西峡源头的梅岐乡辖各村落,近九万亩的森林依靠氧气生存的万物制造出清新的空气。崇尚自然的林农,一代又一代人对森林,保持对山水的敬畏,在经历了历史的一次次人类生存洗礼后,保留了大山的那份原始与人类生存的取舍。在梅岐的大山深处至今保留着原始成片的森林,古树群,林木有南方红豆杉、华南石、林叶蕨、苦槠、钩粟等,树龄达600年以上。茂密的原始森林,成了珍稀动物的家园。一些古老的动物得以在森林里繁衍生息了下来。森林中发现的有猕猴、穿山甲、黑鹿、白颈长尾雉、黄腹角雉等,峡谷的小溪中有娃娃鱼、鼋、石斑鱼等鱼类。不论是森林中的名贵树木,还是小溪、山坑中的各类鱼类,他们和人类一样都离不开水,水是生命之源。森林是储水池,偌大的成片的原始森林,储备了动植物所需的水,自然在四季轮回中,森林在大地上生生不息,万物与人类共生着,森林才变得如此神秘。
在梅岐乡的各村落,自从有人类在此密林里和小溪冲击河谷,一些平坦的山坳地,开基建村,居守家园,开田整地,看护山林,种植林木,经营森林。历经一代代村民、林农的习成养就许多具有林业地区相近而又不近相同的植树造林传统习俗。有的林农夫妇如果头胎生了女儿,就要在自家的荒山或田头地角栽几棵杉树,称“嫁妆树”,等女儿出嫁时,树木也已成林,用来制作女儿陪嫁的嫁妆。而有的村落,有的村民,有的林农夫妇如果头胎生了儿子,更为隆重,要给儿子栽“三旦树”,在儿子出生第三日时要请亲朋好友吃“三旦酒”,又是植树节气时,顺便请几个亲朋好友栽几片森林,待日后成材,由长子分配盖或修缮房屋之用。在梅岐乡域,不但植树有其习俗,护树也有其习俗。比如,入冬冬收结束后,林农一般在晴天,都是上山看护自家的林木、毛竹林等。有“冬整枝,不伤树”之说,通过冬天整枝,促使森林能够快速成林,毛竹则留优除劣,来年春天长出粗壮的毛竹。旧时的林农,在“靠山吃山”的生存环境下,有了他们从历代传承下来的习俗,延续当地林业的更迭和发展。而今,偌大的梅岐乡留守在村的青壮村民极少,森林更多的回归了自然生长,封山已是常态,未来的森林将更加接近自然,人为的索取将越越来越少。
走进梅岐,茂密的森林令人神往。森林里的万物,有许多是人类未知的,需要人类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去探索,森林不仅给人类带来清新的空气,更给人类带来无限的神秘。梅岐的前世和今生,与森林结缘。每逢春夏雨季,大地上的森林和天上的白云连在一起,胜似仙境,分不清天南地北。云中的森林,会在行走四方的游子梦里头显现,五彩缤纷的世界,人类需要森林,森林需要人类的呵护,相依谐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