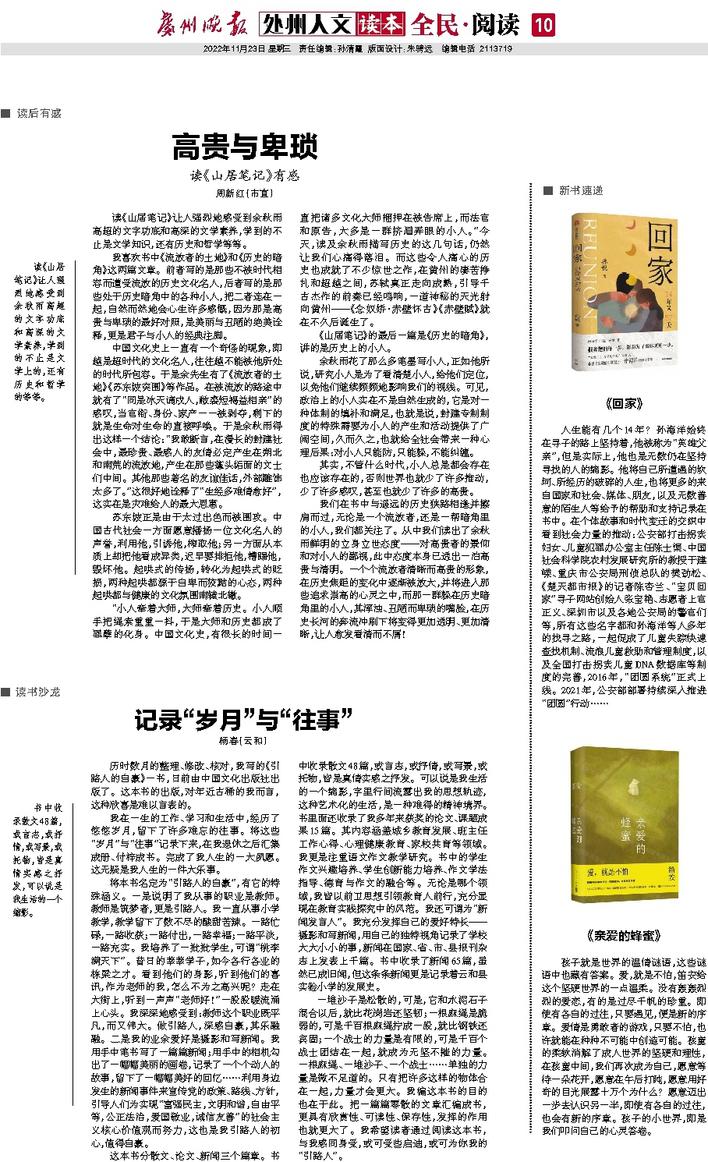周新红(市直)
读《山居笔记》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余秋雨高超的文字功底和高深的文学素养,学到的不止是文学知识,还有历史和哲学等等。
我喜欢书中《流放者的土地》和《历史的暗角》这两篇文章。前者写的是那些不被时代相容而遭受流放的历史文化名人,后者写的是那些处于历史暗角中的各种小人,把二者连在一起,自然而然地会心生许多感慨,因为那是高贵与卑琐的最好对照,是美丽与丑陋的绝美诠释,更是君子与小人的经典注脚。
中国文化史上一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即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被他所处的时代所包容。于是余先生有了《流放者的土地》《苏东坡突围》等作品。在被流放的路途中就有了“同是冰天谪戍人,敝裘短褐益相亲”的感叹,当官衔、身份、家产一一被剥夺,剩下的就是生命对生命的直接呼唤。于是余秋雨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敢断言,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最珍贵、最感人的友情必定产生在朔北和南荒的流放地,产生在那些蓬头垢面的文士们中间。其他那些著名的友谊佳话,外部雕饰太多了。”这很好地诠释了“生经多难情愈好”,这实在是灾难给人的最大恩惠。
苏东坡正是由于太过出色而被围攻。中国古代社会一方面愿意播扬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引诱他,榨取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看成异类,迟早要排拒他,糟蹋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源于自卑而狡黠的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
“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中国文化史,有很长的时间一直把诸多文化大师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挤眉弄眼的小人。”今天,读及余秋雨描写历史的这几句话,仍然让我们心痛得落泪。而这些令人痛心的历史也成就了不少惊世之作,在黄州的凄苦挣扎和超越之间,苏轼真正走向成熟,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就在不久后诞生了。
《山居笔记》的最后一篇是《历史的暗角》,讲的是历史上的小人。
余秋雨花了那么多笔墨写小人,正如他所说,研究小人是为了看清楚小人,给他们定位,以免他们继续频频地影响我们的视线。可见,政治上的小人实在不是自然生成的,它是对一种体制的填补和满足,也就是说,封建专制制度的特殊需要为小人的产生和活动提供了广阔空间,久而久之,也就给全社会带来一种心理后果:对小人只能防,只能躲,不能纠缠。
其实,不管什么时代,小人总是都会存在也应该存在的,否则世界也就少了许多推动,少了许多感叹,甚至也就少了许多的高贵。
我们在书中与遥远的历史狭路相逢并擦肩而过,无论是一个流放者,还是一帮暗角里的小人,我们都关注了。从中我们读出了余秋雨鲜明的立身立世态度——对高贵者的景仰和对小人的鄙视,此中态度本身已透出一泊高贵与清明。一个个流放者清晰而高贵的形象,在历史焦距的变化中逐渐被放大,并将进入那些追求崇高的心灵之中,而那一群躲在历史暗角里的小人,其浑浊、丑陋而卑琐的嘴脸,在历史长河的奔流冲刷下将变得更加透明、更加清晰,让人愈发看清而不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