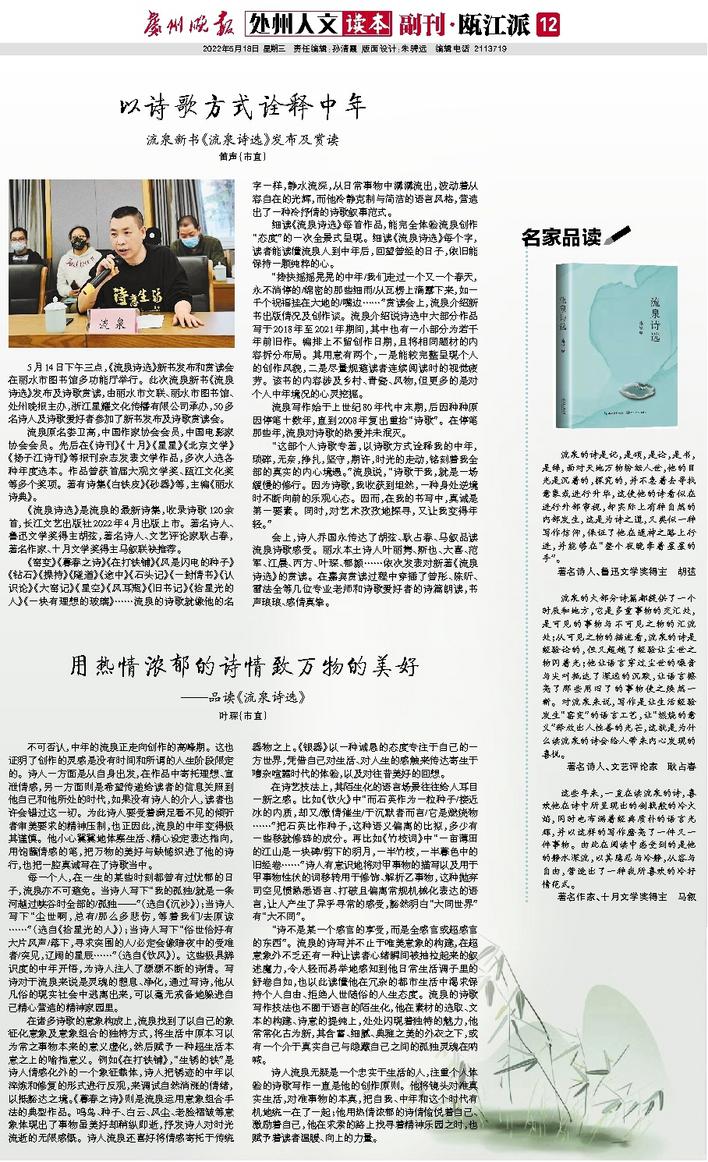叶琛(市直)
不可否认,中年的流泉正走向创作的高峰期。这也证明了创作的灵感是没有时间和所谓的人生阶段限定的。诗人一方面是从自身出发,在作品中寄托理想、宣泄情感,另一方面则是希望传递给读者的信息关照到他自己和他所处的时代,如果没有诗人的介入,读者也许会错过这一切。为此诗人要受着满足看不见的倾听者审美要求的精神压制,也正因此,流泉的中年变得极其谨慎。他小心翼翼地体察生活、精心设定表达指向,用饱蘸情感的笔,把万物的美好与缺憾织进了他的诗行,也把一腔真诚写在了诗歌当中。
每一个人,在一生的某些时刻都曾有过忧郁的日子,流泉亦不可避免。当诗人写下“我的孤独/就是一条河越过峡谷时全部的/孤独——”(选自《沉沙》);当诗人写下“尘世啊,总有/那么多悲伤,等着我们/去原谅……”(选自《拾星光的人》);当诗人写下“俗世恰好有大片风声/落下,寻求突围的人/必定会像暗夜中的受难者/突见,辽阔的星辰……”(选自《饮风》)。这些极具辨识度的中年开悟,为诗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诗情。写诗对于流泉来说是灵魂的憩息、净化,通过写诗,他从凡俗的现实社会中逃离出来,可以毫无戒备地躲进自己精心营造的精神家园里。
在诸多诗歌的意象构成上,流泉找到了以自己的象征化意象及意象组合的独特方式,将生活中原本习以为常之事物本来的意义虚化,然后赋予一种超生活本意之上的喻指意义。例如《在打铁铺》,“生锈的铁”是诗人情感化外的一个象征载体,诗人把锈迹的中年以淬炼和修复的形式进行反观,来调试自然消涨的情绪,以抵豁达之境。《暮春之诗》则是流泉运用意象组合手法的典型作品。鸣鸟、种子、白云、风尘、老脸褶皱等意象体现出了事物虽美好却稍纵即逝,抒发诗人对时光流逝的无限感慨。诗人流泉还喜好将情感寄托于传统器物之上。《银器》以一种诚恳的态度专注于自己的一方世界,凭借自己对生活、对人生的感触来传达寄生于嘈杂喧嚣时代的体验,以及对往昔美好的回想。
在诗艺技法上,其陌生化的语言场景往往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比如《饮火》中“而石英作为一粒种子/接近冰的内质,却又/激情催生/于沉默者而言/它是燃烧物……”把石英比作种子,这种语义偏离的比拟,多少有一些移就修辞的成分。再比如《竹枝词》中“一亩薄田的江山是一块碑/剪下的明月,一半竹枝,一半暮色中的旧经卷……”诗人有意识地将对甲事物的描写以及用于甲事物性状的词移转用于修饰、解析乙事物,这种抛弃司空见惯熟悉语言、打破且偏离常规机械化表达的语言,让人产生了异乎寻常的感受,豁然明白“大同世界”有“大不同”。
“诗不是某一个感官的享受,而是全感官或超感官的东西”。流泉的诗写并不止于唯美意象的构建,在超意象外不乏还有一种让读者心绪瞬间被抽拉起来的叙述魔力,令人轻而易举地感知到他日常生活调子里的舒卷自如,也以此读懂他在冗杂的都市生活中渴求保持个人自由、拒绝入世随俗的人生态度。流泉的诗歌写作技法也不囿于语言的陌生化,他在素材的选取、文本的构建、诗意的提纯上,处处闪现着独特的魅力,他常常化古为新,其含蓄、细腻、典雅之美的外衣之下,或有一个介于真实自己与隐藏自己之间的孤独灵魂在呐喊。
诗人流泉无疑是一个忠实于生活的人,注重个人体验的诗歌写作一直是他的创作原则。他将镜头对准真实生活,对准事物的本真,把自我、中年和这个时代有机地统一在了一起;他用热情浓郁的诗情愉悦着自己、激励着自己,他在求索的路上找寻着精神乐园之时,也赋予着读者温暖、向上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