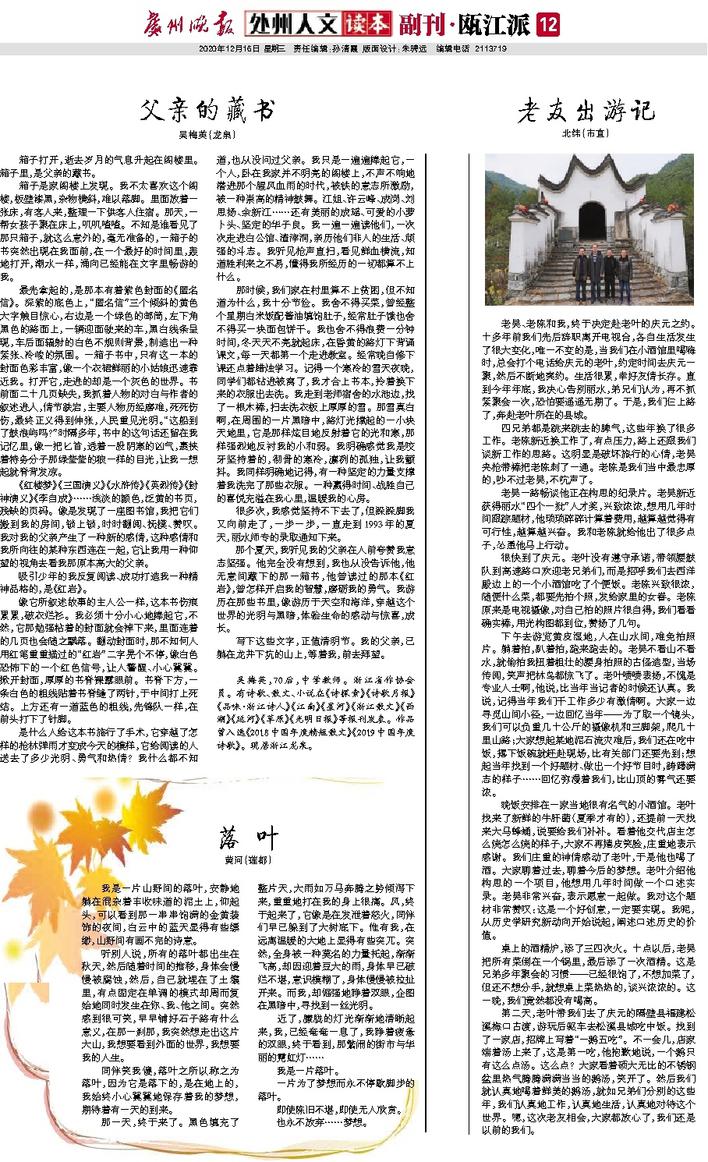吴梅英(龙泉)
箱子打开,逝去岁月的气息升起在阁楼里。箱子里,是父亲的藏书。
箱子是家阁楼上发现。我不太喜欢这个阁楼,板壁漆黑,杂物横斜,难以落脚。里面放着一张床,有客人来,整理一下供客人住宿。那天,一帮女孩子聚在床上,叽叽喳喳。不知是谁看见了那只箱子,就这么意外的,毫无准备的,一箱子的书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在一个最好的时间里,轰地打开,潮水一样,涌向已经能在文字里畅游的我。
最先拿起的,是那本有着紫色封面的《匿名信》。深紫的底色上,“匿名信”三个倾斜的黄色大字触目惊心,右边是一个绿色的邮筒,左下角黑色的路面上,一辆迎面驶来的车,黑白线条呈现,车后面辐射的白色不规则背景,制造出一种紧张、冷峻的氛围。一箱子书中,只有这一本的封面色彩丰富,像一个衣裙鲜丽的小姑娘迅速靠近我。打开它,走进的却是一个灰色的世界。书前面二十几页缺失,我抓着人物的对白与作者的叙述进入,情节跌宕,主要人物历经磨难,死死伤伤,最终正义得到伸张,人民重见光明。“这船到了鼓浪屿吗?”时隔多年,书中的这句话还留在我记忆里,像一把匕首,透着一股阴寒的凶气,裹挟着特务分子那绿莹莹的狼一样的目光,让我一想起就脊背发凉。
《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英烈传》《封神演义》《李自成》……浅淡的颜色,泛黄的书页,残缺的页码。像是发现了一座图书馆,我把它们搬到我的房间,锁上锁,时时翻阅、抚摸、赞叹。我对我的父亲产生了一种新的感情,这种感情和我所向往的某种东西连在一起,它让我用一种仰望的视角去看我那原本高大的父亲。
吸引少年的我反复阅读、成功打造我一种精神品格的,是《红岩》。
像它所叙述故事的主人公一样,这本书伤痕累累,破衣烂衫。我必须十分小心地捧起它,不然,它那勉强粘着的封面就会掉下来,里面连着的几页也会随之飘落。翻动封面时,那不知何人用红笔重重描过的“红岩”二字晃个不停,像白色恐怖下的一个红色信号,让人警醒、小心翼翼。掀开封面,厚厚的书脊裸露眼前。书脊下方,一条白色的粗线贴着书脊缝了两针,于中间打上死结。上方还有一道蓝色的粗线,先锋队一样,在前头打下了针脚。
是什么人给这本书施行了手术,它穿越了怎样的枪林弹雨才变成今天的模样,它给阅读的人送去了多少光明、勇气和热情?我什么都不知道,也从没问过父亲。我只是一遍遍捧起它,一个人,卧在我家并不明亮的阁楼上,不声不响地潜进那个腥风血雨的时代,被铁的意志所激励,被一种崇高的精神鼓舞。江姐、许云峰、成岗、刘思扬、余新江……还有美丽的成瑶、可爱的小萝卜头、坚定的华子良。我一遍一遍读他们,一次次走进白公馆、渣滓洞,亲历他们非人的生活、顽强的斗志。我听见枪声直扫,看见鲜血横流,知道胜利来之不易,懂得我所经历的一切都算不上什么。
那时候,我们家在村里算不上贫困,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十分节俭。我舍不得买菜,曾经整个星期白米饭配酱油填饱肚子,经常肚子饿也舍不得买一块面包饼干。我也舍不得浪费一分钟时间,冬天天不亮就起床,在昏黄的路灯下背诵课文,每一天都第一个走进教室。经常晚自修下课还点着蜡烛学习。记得一个寒冷的雪天夜晚,同学们都钻进被窝了,我才合上书本,拎着换下来的衣服出去洗。我走到老师宿舍的水池边,找了一根木棒,扫去洗衣板上厚厚的雪。那雪真白啊,在周围的一片黑暗中,路灯光撑起的一小块天地里,它是那样炫目地反射着它的光和寒,那样强烈地反衬我的小和弱。我明确感觉我是咬牙坚持着的,彻骨的寒冷,凛冽的孤独,让我颤抖。我同样明确地记得,有一种坚定的力量支撑着我洗完了那些衣服。一种赢得时间、战胜自己的喜悦充溢在我心里,温暖我的心房。
很多次,我感觉坚持不下去了,但跺跺脚我又向前走了,一步一步,一直走到1993年的夏天,丽水师专的录取通知下来。
那个夏天,我听见我的父亲在人前夸赞我意志坚强。他完全没有想到,我也从没告诉他,他无意间藏下的那一箱书,他曾读过的那本《红岩》,曾怎样开启我的智慧,磨砺我的勇气。我游历在那些书里,像游历于天空和海洋,穿越这个世界的光明与黑暗,体验生命的感动与惊喜,成长。
写下这些文字,正值清明节。我的父亲,已躺在龙井下坑的山上,等着我,前去拜望。
吴梅英,70后,中学教师。浙江省作协会员。有诗歌、散文、小说在《诗探索》《诗歌月报》《品味·浙江诗人》《江南》《星河》《浙江散文》《西湖》《延河》《草原》《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作品曾入选《2018中国年度精短散文》《2019中国年度诗歌》。现居浙江龙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