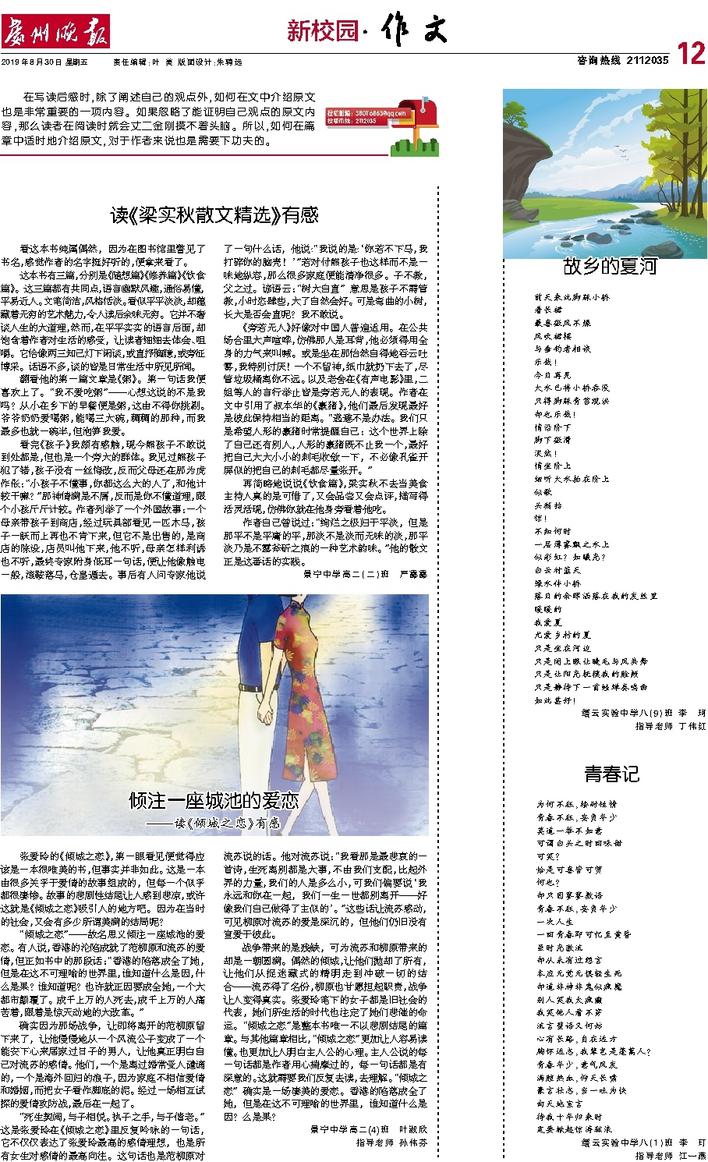看这本书纯属偶然,因为在图书馆里瞥见了书名,感觉作者的名字挺好听的,便拿来看了。
这本书有三篇,分别是《随想篇》《修养篇》《饮食篇》。这三篇都有共同点,语言幽默风趣,通俗易懂,平易近人。文笔简洁,风格恬淡。看似平平淡淡,却蕴藏着无穷的艺术魅力,令人读后余味无穷。它并不奢谈人生的大道理,然而,在平平实实的语言后面,却饱含着作者对生活的感受,让读者细细去体会、咀嚼。它恰像两三知己灯下闲谈,或直抒胸臆,或旁征博采。话语不多,谈的皆是日常生活中所见所闻。
翻看他的第一篇文章是《粥》。第一句话我便喜欢上了。“我不爱吃粥”——心想这说的不是我吗?从小在乡下的早餐便是粥,这由不得你挑剔。爷爷奶奶爱喝粥,能喝三大碗,稠稠的那种,而我最多也就一碗半,但泡笋我爱。
看完《孩子》我颇有感触,现今熊孩子不敢说到处都是,但也是一个旁大的群体。我见过熊孩子犯了错,孩子没有一丝悔改,反而父母还在那为虎作伥:“小孩子不懂事,你都这么大的人了,和他计较干嘛?”那神情满是不屑,反而是你不懂道理,跟个小孩斤斤计较。作者列举了一个外国故事:一个母亲带孩子到商店,经过玩具部看见一匹木马,孩子一跃而上再也不肯下来,但它不是出售的,是商店的陈设,店员叫他下来,他不听,母亲怎样利诱也不听,最终专家附身低耳一句话,便让他像触电一般,滚鞍落马,仓皇遁去。事后有人问专家他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我说的是:‘你若不下马,我打碎你的脑壳!’”若对付熊孩子也这样而不是一味地纵容,那么很多家庭便能清净很多。子不教,父之过。谚语云:“树大自直”意思是孩子不需管教,小时恣肆些,大了自然会好。可是弯曲的小树,长大是否会直呢?我不敢说。
《旁若无人》好像对中国人普遍适用。在公共场合里大声喧哗,仿佛那人是耳背,他必须得用全身的力气来叫喊。或是坐在那怡然自得地吞云吐雾,我特别讨厌!一个不留神,纸巾就扔下去了,尽管垃圾桶离你不远。以及老舍在《有声电影》里,二姐等人的言行举止皆是旁若无人的表现。作者在文中引用了叔本华的《豪猪》,他们最后发现最好是彼此保持相当的距离。“逃避不是办法。我们只是希望人形的豪猪时常提醒自己:这个世界上除了自己还有别人,人形的豪猪既不止我一个,最好把自己大大小小的刺毛收敛一下,不必像孔雀开屏似的把自己的刺毛都尽量张开。”
再简略地说说《饮食篇》,梁实秋不去当美食主持人真的是可惜了,又会品尝又会点评,描写得活灵活现,仿佛你就在他身旁看着他吃。
作者自己曾说过:“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但是那平不是平庸的平,那淡不是淡而无味的淡,那平淡乃是不露斧斫之痕的一种艺术韵味。”他的散文正是这番话的实践。
景宁中学高二(二)班 严露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