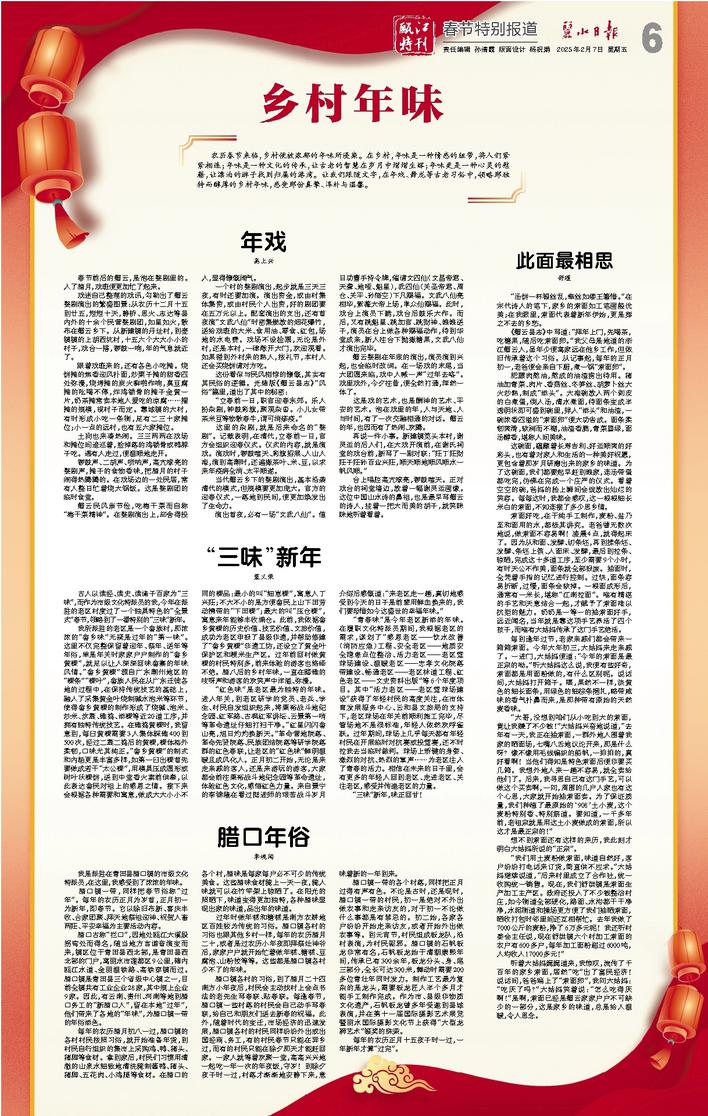高上兴
春节前后的缙云,是泡在婺剧里的。入了腊月,戏班便更加忙了起来。
戏迷自己整理的戏讯,勾勒出了缙云婺剧演出的繁盛图景:从农历十二月十五到廿五,短短十天,静桥、思火、志达等县内外的十余个民营婺剧团,如星如火,散布在缙云乡下。从新建镇的丹址村,到壶镇镇的上胡西坑村,十五六个大大小小的村子,戏台一搭,锣鼓一响,年的气息就近了。
跟着戏班来的,还有各色小吃摊。烧饼摊的焦香迎风扑面,炒栗子摊的甜香四处弥漫,烧烤摊的炭火噼啪作响,臭豆腐摊的吆喝不停,炸鸡锁骨的摊子金黄一片,奶茶摊常卖本地人爱吃的凉腐……摆摊的规模,视村子而定。靠城镇的大村,有时形成小吃一条街,足有二三十家摊位;小一点的远村,也有五六家摊位。
土狗也来凑热闹。三三两两在戏场和摊位间逡巡着,捡掉落的鸡锁骨或鸭脖子吃。遇有人走过,便温顺地走开。
锣鼓声、二胡声、唢呐声,高亢嘹亮的婺剧声,摊子的食物香味,把腊月的村子闹得热腾腾的。在戏场边的一处民居,常有人整日忙着烧大锅饭。这是婺剧团的临时食堂。
缙云民风崇节俭,吃梅干菜而自称“梅干菜精神”。在婺剧演出上,却舍得投入,显得慷慨阔气。
一个村的婺剧演出,起步就是三天三夜,有时还要加演。演出资金,或由村集体集资,或由村民个人出资,好的剧团要在五万元以上。配套演出的支出,还有首夜演“文武八仙”时密集燃放的烟花爆竹,送给戏班的大米、食用油、零食、红包,场地的水电费。戏场不设检票,无论是外村,还是本村,一律敞开大门,欢迎观看。如果碰到外村来的熟人,按礼节,本村人还会买烧饼请对方吃。
这份看似与民风相悖的慷慨,其实有其民俗的逻辑。光绪版《缙云县志》“风俗”篇里,道出了其中的秘密:
“立春前一日,职官迎春东郊。乐人扮杂剧,钟鼓彩旗,聚观杂沓。小儿女带茶米豆等物散春牛,谓可消疹疫。”
这里的杂剧,就是后来命名的“婺剧”。记载表明,在清代,立春前一日,官方会组织迎春仪式。仪式的内容,就是演戏。演戏时,锣鼓喧天、彩旗招展、人山人海,演到高潮时,还遍撒茶叶、米、豆,以求来年疫病全消、太平顺遂。
当代缙云乡下的婺剧演出,基本沿袭清代的模式,但规模要更加庞大。官方的迎春仪式,一落地到民间,便更加焕发出了生命力。
演出首夜,必有一场“文武八仙”。值日功曹手持令牌,催请文四仙(文昌帝君、天聋、地哑、魁星),武四仙(关圣帝君、周仓、关平、孙悟空)下凡赐福。文武八仙亮相毕,紫薇大帝上场,率众仙赐福。此时,戏台上演员下跪,戏台后鼓乐大作。而后,又有跳魁星、跳加官、跳财神、娘娘送子,演员在台上做各种赐福动作,待到华堂成亲,新人往台下抛撒糖果,文武八仙才演出完毕。
缙云婺剧在年底的演出,演员演到兴起,也会临时改词。在一场戏的末尾,当大团圆来临,戏中人喊一声“过年去咯”。戏里戏外,今夕往昔,便全然打通,浑然一体了。
这是戏的艺术,也是酬神的艺术、平安的艺术。泡在戏里的年,人与天地、人与时间,有了一次交融相通的对话。缙云的年,也因而有了热闹、欢腾。
再说一件小事。新建镇笕头本村,谢灵运的后人们,在大戏开演前,在谢氏祠堂的戏台前,新写了一副对联:“旺丁旺财旺子旺孙百业兴旺,顺天顺地顺风顺水一帆风顺。”
台上唱腔高亢嘹亮,锣鼓喧天。正对戏台的祠堂墙边,放着一幅谢灵运画像。这位中国山水诗的鼻祖,也是最早写缙云的诗人,挂着一把大而美的胡子,就笑眯眯地听着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