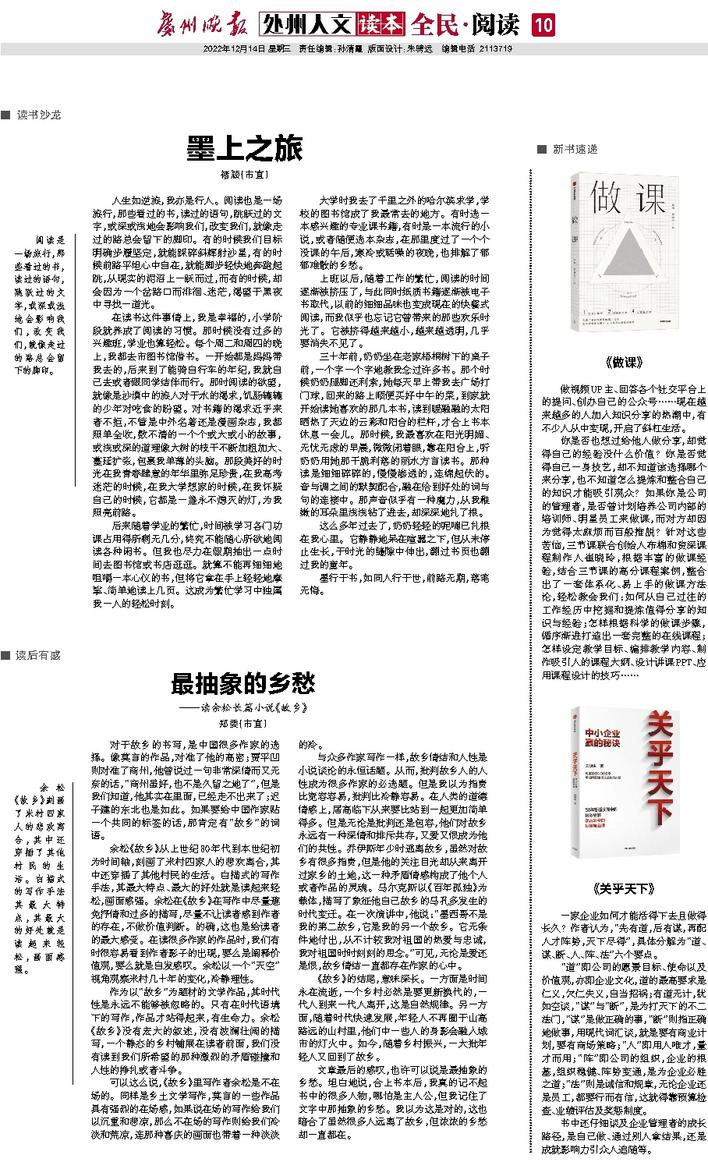对于故乡的书写,是中国很多作家的选择。像莫言的作品,对准了他的高密;贾平凹则对准了商州,他曾说过一句非常深情而又无奈的话,“商州虽好,也不是久留之地了”,但是我们知道,他其实在里面,已经走不出来了;迟子建的东北也是如此。如果要给中国作家贴一个共同的标签的话,那肯定有“故乡”的词语。
余松《故乡》从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为时间轴,刻画了米村四家人的悲欢离合,其中还穿插了其他村民的生活。白描式的写作手法,其最大特点、最大的好处就是读起来轻松,画面感强。余松在《故乡》在写作中尽量避免抒情和过多的描写,尽量不让读者感到作者的存在,不做价值判断。的确,这也是给读者的最大感受。在读很多作家的作品时,我们有时很容易看到作者影子的出现,要么是阐释价值观,要么就是自发感叹。余松以一个“天空”视角观察米村几十年的变化,冷静理性。
作为以“故乡”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其时代性是永远不能够被忽略的。只有在时代语境下的写作,作品才站得起来,有生命力。余松《故乡》没有宏大的叙述,没有波澜壮阔的描写,一个静态的乡村铺展在读者前面,我们没有读到我们所希望的那种激烈的矛盾碰撞和人性的挣扎或者斗争。
可以这么说,《故乡》里写作者余松是不在场的。同样是乡土文学写作,莫言的一些作品具有强烈的在场感,如果说在场的写作给我们以沉重和悲凉,那么不在场的写作则给我们冷淡和荒凉,连那种喜庆的画面也带着一种淡淡的冷。
与众多作家写作一样,故乡情结和人性是小说谈论的永恒话题。从而,批判故乡人的人性成为很多作家的必选题。但是我以为指责比宽容容易,批判比冷静容易。在人类的道德情感上,居高临下从来要比站到一起更加简单得多。但是无论是批判还是包容,他们对故乡永远有一种深情和排斥共存,又爱又恨成为他们的共性。乔伊斯年少时逃离故乡,虽然对故乡有很多指责,但是他的关注目光却从来离开过家乡的土地,这一种矛盾情感构成了他个人或者作品的灵魂。马尔克斯以《百年孤独》为载体,描写了象征他自己故乡的马孔多发生的时代变迁。在一次演讲中,他说:“墨西哥不是我的第二故乡,它是我的另一个故乡。它无条件地付出,从不计较我对祖国的热爱与忠诚,我对祖国时时刻刻的思念。”可见,无论是爱还是恨,故乡情结一直都存在作家的心中。
《故乡》的结尾,意味深长。一方面是时间永在流逝,一个乡村必然是要更新换代的,一代人到来一代人离开,这是自然规律。另一方面,随着时代快速发展,年轻人不再囿于山高路远的山村里,他们中一些人的身影会融入城市的灯火中。如今,随着乡村振兴,一大批年轻人又回到了故乡。
文章最后的感叹,也许可以说是最抽象的乡愁。坦白地说,合上书本后,我真的记不起书中的很多人物,哪怕是主人公,但我记住了文字中那抽象的乡愁。我以为这是对的,这也暗合了虽然很多人远离了故乡,但浓浓的乡愁却一直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