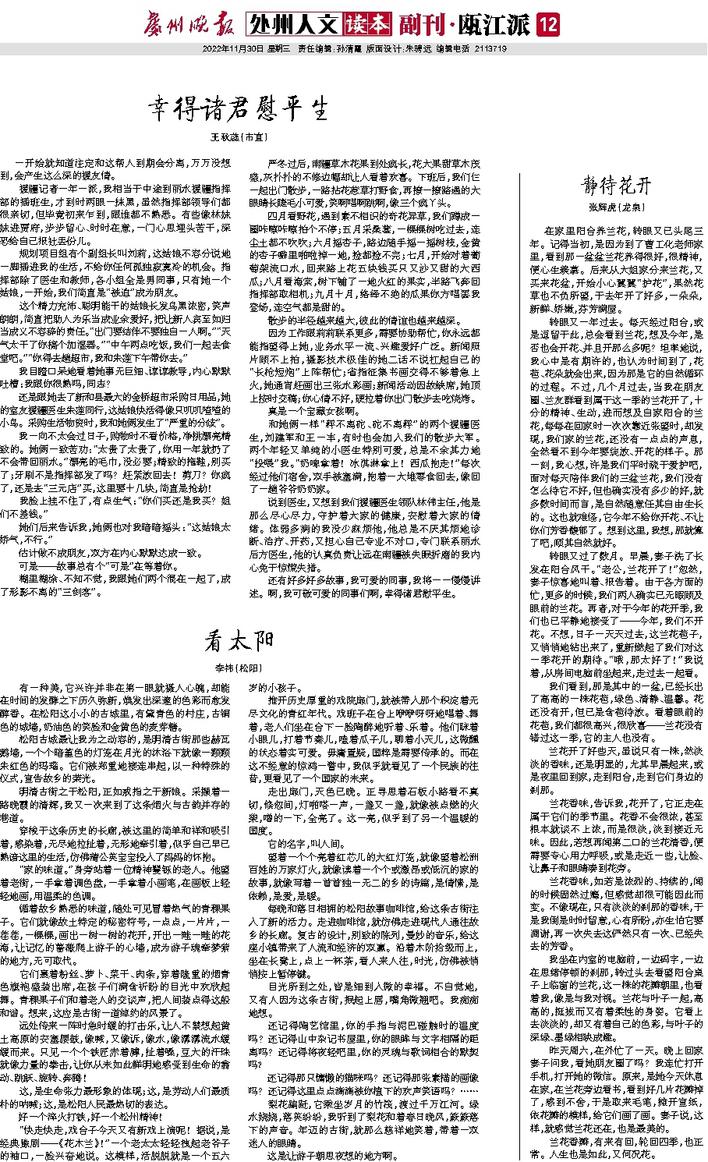李祎(松阳)
有一种美,它兴许并非在第一眼就摄人心魄,却能在时间的发酵之下历久弥新,焕发出深邃的色彩而愈发醇香。在松阳这小小的古城里,有黛青色的村庄,古铜色的城墙,奶油色的笑脸和金黄色的麦芽糖。
松阳古城最让我为之动容的,是明清古街那些赫瓦鹅墙,一个个暗堇色的灯笼在月光的沐浴下就像一颗颗朱红色的玛瑙。它们被郑重地接连串起,以一种特殊的仪式,宣告故乡的荣光。
明清古街之于松阳,正如戒指之于新娘。采撷着一路晚霞的清辉,我又一次来到了这条烟火与古韵并存的巷道。
穿梭于这条历史的长廊,被这里的简单和祥和吸引着,感染着,无尽地拉扯着,无形地牵引着,似乎自己早已熟谙这里的生活,仿佛蒲公英宝宝投入了妈妈的怀抱。
“家的味道。”身旁站着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他望着老街,一手拿着调色盘,一手拿着小画笔,在画板上轻轻地画,用温柔的色调。
循着故乡熟悉的味道,随处可见冒着热气的青稞果子。它们就像故土特定的秘密符号,一点点,一片片,一茬茬,一棵棵,画出一树一树的花开,开出一畦一畦的花海,让记忆的蔷薇爬上游子的心墙,成为游子魂牵梦萦的地方,无可取代。
它们裹着粉丝、萝卜、菜干、肉条,穿着隆重的烟青色旗袍盛装出席,在孩子们满含祈盼的目光中欢欣起舞。青稞果子们和着老人的交谈声,把人间装点得这般和谐。想来,这应是古街一道绰约的风景了。
远处传来一阵时急时缓的打击乐,让人不禁想起黄土高原的安塞腰鼓,像喊,又像诉,像水,像潺潺流水缓缓而来。只见一个个铁匠赤着膊,扯着嗓,豆大的汗珠就像力量的拳击,让你从未如此鲜明地感受到生命的翕动、跳跃、旋转、奔腾!
这,是生命张力最形象的体现;这,是劳动人们最质朴的呐喊;这,是松阳人民最热切的表达。
好一个淬火打铁,好一个松州精神!
“快走快走,戏台子今天又有新戏上演呢!据说,是经典豫剧——《花木兰》!”一个老太太轻轻拽起老爷子的袖口,一脸兴奋地说。这模样,活脱脱就是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子。
推开历史厚重的戏院扉门,就被带入那个积淀着无尽文化的青红年代。戏班子在台上咿咿呀呀地唱着、舞着,老人们坐在台下一脸陶醉地听着、乐着。他们眯着小眼儿,打着节奏儿,嗑着瓜子儿,聊着小天儿,这微醺的状态着实可爱。毋庸置疑,国粹是需要传承的。而在这不经意的惊鸿一瞥中,我似乎就看见了一个民族的往昔,更看见了一个国家的未来。
走出扉门,天色已晚。正寻思着石板小路看不真切,倏忽间,灯啪嗒一声,一盏又一盏,就像被点燃的火柴,噌的一下,全亮了。这一亮,似乎到了另一个温暖的国度。
它的名字,叫人间。
望着一个个亮着红芯儿的大红灯笼,就像望着松洲百姓的万家灯火,就像读着一个个或激昂或低沉的家的故事,就像写着一首首独一无二的乡的诗篇,是情愫,是依赖,是爱,是暖。
每晚和落日相拥的松阳故事咖啡馆,给这条古街注入了新的活力。走进咖啡馆,就仿佛走进现代人通往故乡的长廊。复古的设计,别致的陈列,曼妙的音乐,给这座小镇带来了人流和经济的双赢。沿着木阶拾级而上,坐在长凳上,点上一杯茶,看人来人往,时光,仿佛被悄悄按上暂停键。
目光所到之处,皆是细到入微的幸福。不自觉地,又有人因为这条古街,抿起上唇,嘴角微翘吧。我痴痴地想。
还记得陶艺馆里,你的手指与泥巴碰触时的温度吗?还记得山中杂记书屋里,你的眼眸与文字相隔的距离吗?还记得将夜轻吧里,你的灵魂与歌词相合的默契吗?
还记得那只慵懒的猫咪吗?还记得那张素描的画像吗?还记得这里点点滴滴被你植下的欢声笑语吗?……
梨花蹁跹,它乘坐岁月的竹筏,渡过千万江河。绿水娆娆,落英纷纷,我听到了梨花和着春日晚风,簌簌落下的声音。年迈的古街,就那么慈祥地笑着,带着一双迷人的眼睛。
这是让游子朝思夜想的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