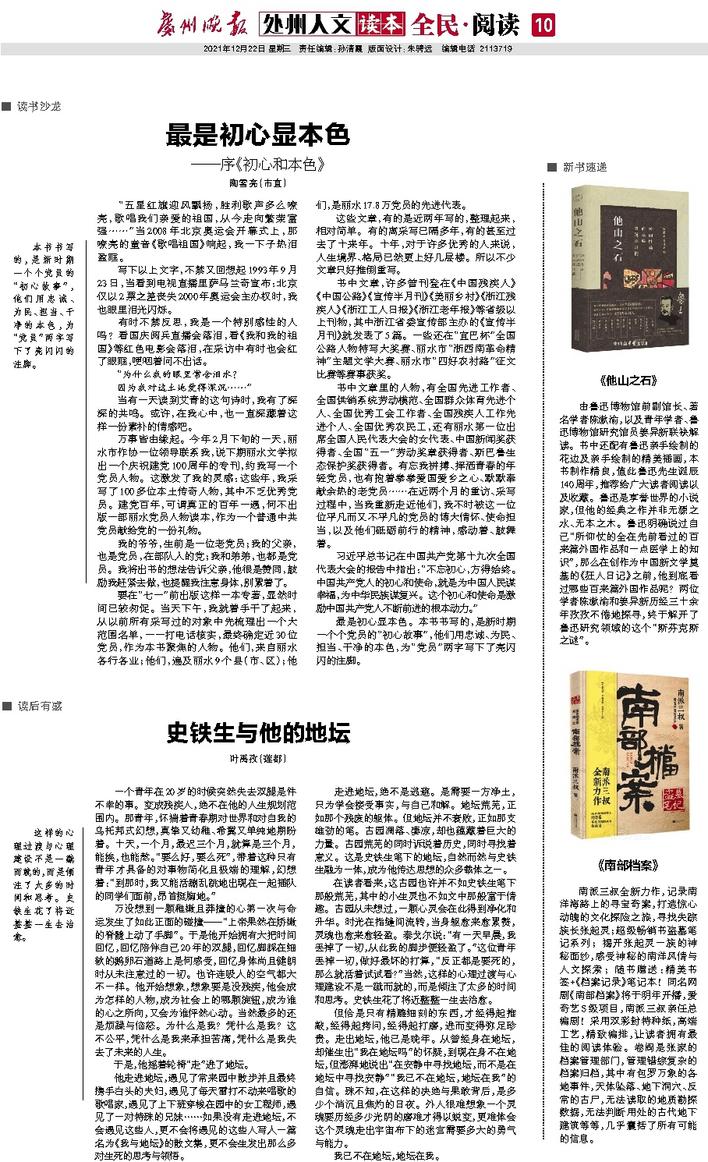叶禹孜(莲都)
一个青年在20岁的时候突然失去双腿是件不幸的事。变成残疾人,绝不在他的人生规划范围内。那青年,怀揣着青春期对世界和对自我的乌托邦式幻想,真挚又幼稚、希冀又单纯地期盼着。十天,一个月,最迟三个月,就算是三个月,能挨,也能熬。“要么好,要么死”,带着这种只有青年才具备的对事物简化且极端的理解,幻想着:“到那时,我又能活蹦乱跳地出现在一起插队的同学们面前,昂首挺胸地。”
万没想到一颗稚嫩且莽撞的心第一次与命运发生了如此正面的碰撞——“上帝果然在娇嫩的脊髓上动了手脚”。于是他开始拥有大把时间回忆,回忆陪伴自己20年的双腿,回忆脚踩在细软的鹅卵石道路上是何感受,回忆身体尚且健朗时从未注意过的一切。也许连吸入的空气都大不一样。他开始想象,想象要是没残疾,他会成为怎样的人物,成为社会上的哪颗旋钮,成为谁的心之所向,又会为谁怦然心动。当然最多的还是烦躁与恼怒。为什么是我?凭什么是我?这不公平,凭什么是我来承担苦痛,凭什么是我失去了未来的人生。
于是,他摇着轮椅“走”进了地坛。
他走进地坛,遇见了常来园中散步并且最终携手白头的夫妇,遇见了每天雷打不动来唱歌的歌唱家,遇见了上下班穿梭在园中的女工程师,遇见了一对特殊的兄妹……如果没有走进地坛,不会遇见这些人,更不会将遇见的这些人写入一篇名为《我与地坛》的散文集,更不会生发出那么多对生死的思考与领悟。
走进地坛,绝不是逃避。是需要一方净土,只为学会接受事实,与自己和解。地坛荒芜,正如那个残废的躯体。但地坛并不衰败,正如那支雄劲的笔。古园凋落、凄凉,却也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古园荒芜的同时诉说着历史,同时寻找着意义。这是史铁生笔下的地坛,自然而然与史铁生融为一体,成为他传达思想的众多载体之一。
在读者看来,这古园也许并不如史铁生笔下那般荒芜,其中的小生灵也不如文中那般富于情趣。古园从未想过,一颗心灵会在此得到净化和升华。时光在指缝间流转,当身躯愈来愈累赘,灵魂也愈来愈轻盈。泰戈尔说:“有一天早晨,我丢掉了一切,从此我的脚步便轻盈了。”这位青年丢掉一切,做好最坏的打算,“反正都是要死的,那么就活着试试看?”当然,这样的心理过渡与心理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倾注了太多的时间和思考。史铁生花了将近整整一生去治愈。
但恰是只有精雕细刻的东西,才经得起推敲,经得起拷问,经得起打磨,进而变得弥足珍贵。走出地坛,他已是晚年。从曾经身在地坛,却催生出“我在地坛吗”的怀疑,到现在身不在地坛,但澎湃地说出“在安静中寻找地坛,而不是在地坛中寻找安静”“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的自信。殊不知,在这样的决绝与果敢背后,是多少个消沉且焦灼的日夜。外人很难想象一个灵魂要历经多少光阴的磨难才得以蜕变,更难体会这个灵魂走出宇宙布下的迷宫需要多大的勇气与能力。
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
这样的心理过渡与心理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倾注了太多的时间和思考。史铁生花了将近整整一生去治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