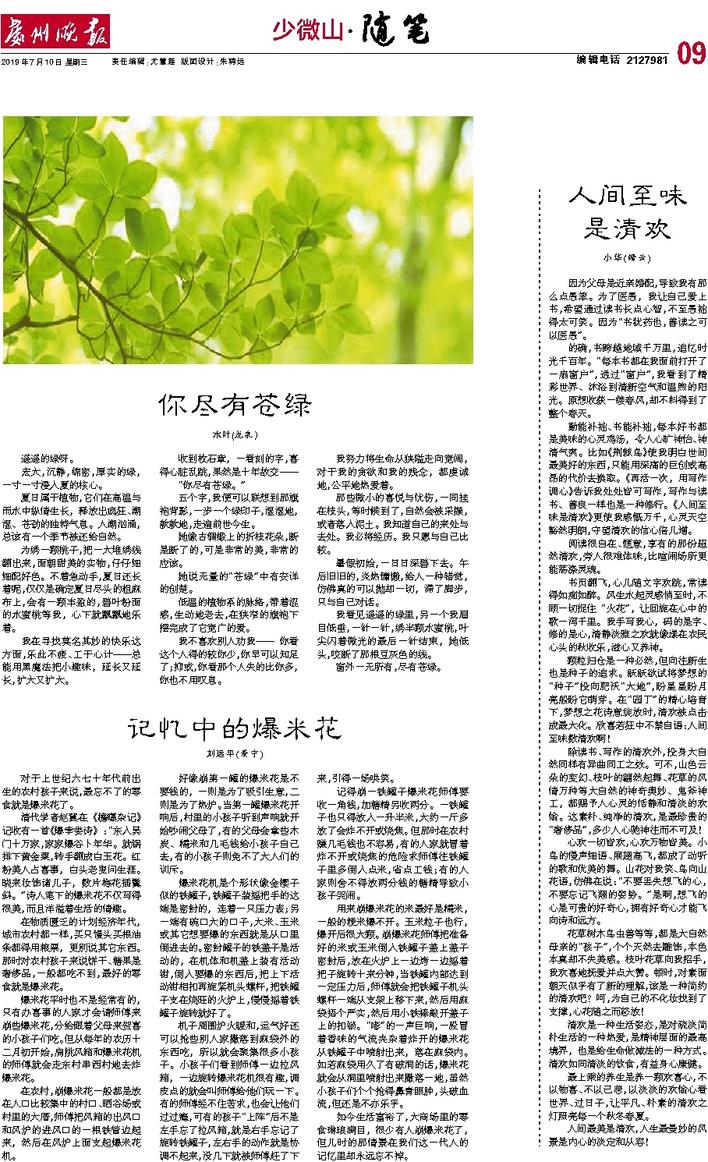刘远平(景宁)
对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前出生的农村孩子来说,最忘不了的零食就是爆米花了。
清代学者赵翼在《檐曝杂记》记收有一首《爆孛娄诗》 :“东入吴门十万家,家家爆谷卜年华。就锅排下黄金粟,转手翻成白玉花。红粉美人占喜事,白头老叟问生涯。晓来妆饰诸儿子,数片梅花插鬓斜。”诗人笔下的爆米花不仅写得很美,而且洋溢着生活的情趣。
在物质匮乏的计划经济年代,城市农村都一样,买只馒头买根油条都得用粮票,更别说其它东西。那时对农村孩子来说饼干、糖果是奢侈品,一般都吃不到,最好的零食就是爆米花。
爆米花平时也不是经常有的,只有办喜事的人家才会请师傅来崩些爆米花,分给跟着父母来贺喜的小孩子们吃。但从每年的农历十二月初开始,肩挑风箱和爆米花机的师傅就会走东村串西村地去炸爆米花。
在农村,崩爆米花一般都是放在人口比较集中的村口、晒谷场或村里的大厝,师傅把风箱的出风口和风炉的进风口的一根铁管边起来,然后在风炉上面支起爆米花机。
好像崩第一罐的爆米花是不要钱的,一则是为了吸引生意,二则是为了热炉。当第一罐爆米花开响后,村里的小孩子听到声响就开始吵闹父母了,有的父母会拿些木炭、糯米和几毛钱给小孩子自己去,有的小孩子则免不了大人们的训斥。
爆米花机是个形状像金樱子似的铁罐子,铁罐子装摇把手的这端是密封的,连着一只压力表;另一端有碗口大的口子,大米、玉米或其它想要爆的东西就是从口里倒进去的。密封罐子的铁盖子是活动的,在机体和机盖上装有活动钳,倒入要爆的东西后,把上下活动钳相扣再旋紧机头螺杆,把铁罐子支在烧旺的火炉上,慢慢摇着铁罐子旋转就好了。
机子周围炉火暖和,运气好还可以抢些别人家撒落到麻袋外的东西吃,所以就会聚集很多小孩子。小孩子们看到师傅一边拉风箱,一边旋转爆米花机很有趣,调皮点的就会叫师傅给他们玩一下。有的师傅经不住苦求,也会让他们过过瘾,可有的孩子“上阵”后不是左手忘了拉风箱,就是右手忘记了旋转铁罐子,左右手的动作就是协调不起来,没几下就被师傅赶了下来,引得一场哄笑。
记得崩一铁罐子爆米花师傅要收一角钱,加糖精另收两分。一铁罐子也只得放入一升半米,大约一斤多放了会炸不开或烧焦。但那时在农村赚几毛钱也不容易,有的人家就冒着炸不开或烧焦的危险求师傅往铁罐子里多倒入点米,省点工钱;有的人家则舍不得放两分钱的糖精导致小孩子哭闹。
用来崩爆米花的米最好是糯米,一般的粳米爆不开。玉米粒子也行,爆开后很大颗。崩爆米花师傅把准备好的米或玉米倒入铁罐子盖上盖子密封后,放在火炉上一边烤一边摇着把子旋转十来分钟,当铁罐内部达到一定压力后,师傅就会把铁罐子机头螺杆一端从支架上移下来,然后用麻袋捂个严实,然后用小铁棒敲开盖子上的扣锁。“嘭”的一声巨响,一股冒着香味的气流夹杂着炸开的爆米花从铁罐子中喷射出来,落在麻袋内。如若麻袋用久了有破洞的话,爆米花就会从洞里喷射出来撒落一地,虽然小孩子们个个抢得鼻青眼肿,头破血流,但还是不亦乐乎。
如今生活富裕了,大商场里的零食琳琅满目,很少有人崩爆米花了,但儿时的那情景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里却永远忘不掉。